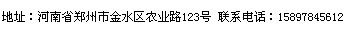托尼middot朱特与20世纪的历史
每个人对待即将到来的死亡态度是不一样的。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得知自己身怀癌症,命不久矣,写了一本书中文翻译为《人之将死》,将自己一辈子写专栏批判的人在书中挨个重新骂一遍,以示一个都不宽恕,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遗产,一种绝不认输的批判精神。
而另外一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身患能让人逐渐瘫痪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之后,开始与死神赛跑的最后的思考与写作,从年到年去世的几年里:他写了一本关于政治和未来生活的道别词《沉疴遍地》;二十余篇有关他私人生活的回忆小品文《记忆小屋》,一份公开的讲义,以及关于二十世纪的历史的全面研究的访谈录《思虑20世纪》。在朱特看来,人之将死,他留下的“善”就是他身为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这是他最后的精神遗产。
现如今,这些著作都摆在我的面前,从他早年留学法国高师,研究二战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未竟的往昔》,到晚年为他在史学界赢得巨大荣誉、短期内无法超越的《战后欧洲史》,以及瘫痪在床极力发出的最后之声,对二十世纪作出总结陈词的《思虑20世纪》。这些清晰的思想脉络,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从未停止过思考的热忱。
现在我们可以说,从朱特的所有著作挑选出一本最佳的入门读物,一定是他与东欧历史学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谈《思虑20世纪》,这本书无愧于是朱特的思想自传。两位都是东欧史学家,有着相近的历史旨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对谈涉及到二十世纪所有知识分子都关心的公共议题,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与大屠杀、马克思主义、冷战等各种议题,都有发人深省的深刻洞见,让我们领略了一位专业历史学家的坦诚和无畏。而且他们的谈话将朱特的家族史、求学史和著述史融为一体,这种奇特的编排方式让读者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对谈的历史,其实就是他们参与创建的历史,他们体验过,经历过,思考过这些议题,所以他们对谈的激情源于他们都是历史中人。
我一直有一个观察,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我们是丧失历史感的一代人。因为所有的历史我们都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我们的生活中不是没有历史,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被限定在各种媒介之中,我们阅读书籍中的历史,观看电视上的历史,查阅网上的历史,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到历史的二手消息和碎片,我们缺乏现场感,也从未想过参与到历史中去。好像历史对于我们只是一个大写而陌生的他者:只是一种由专业的历史学家才能知道的东西。
但是阅读二十世纪很多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写作,我有种强烈的现场感,比如朱特说,年12月,他正在维也纳的出租车上,从广播中听到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库斯垮台的消息,他意识都东欧战后的历史图景正在发生着巨变,而这一切对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影响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没有人开始思考,他认识到,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就这一问题写一部新的著作,这就是他花费十年之功才完成的《战后欧洲史》。
有人评价说,《战后欧洲史》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东欧和中欧史纳入到战后的欧洲版图之中。这个评价只说对了一点,朱特曾服膺于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那是他心目中历史写作的范本,唯一不足的是霍布斯鲍姆献身的党派身份限制了他的历史视野,预设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观念框住甚至扭曲了霍布斯鲍姆在更为宽广的领域内对主题进行深化思考。朱特的历史写作,有意识弥补了霍布斯鲍姆的狭隘不足,他不但提供了一种中东欧视野,还将这种视野引入到欧洲和美国史学的写作范畴中,对常见的进步史学观和线性史学观进行了质疑。
在他看来,历史著作不但要有一流的文体,要讲述一个好故事,更重要的除了历史学家的视野,还要有知识分子思考和一个公民的现实关切。历史是写给人看,对大多数人来说,阅读是一种在想象中参与过去的方式。如果你写的历史书只是为了学院的少数研究者用,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并没有将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带入到现在,对大众产生影响。
我一直强调,一个好的历史学家都要有强烈的历史现场感。比如朱特早年在以色列基布兹农村的生活经历让他从一个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者;年的东欧的“布拉格之春”发生,他意识到革命的存在,自学捷克语,深入东欧观察革命;法国的“六月风暴”发生不久,朱特取得了巴黎高师的奖学金,成为了萨特、阿隆、波伏娃等人的校友,开始了自己对法国史和二战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这些现实发生的大事件都是他早年学术著作的主题,其中《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更值得着重提及。
按照朱特最初的设想,这本书是关于“二战”之后巴黎左翼知识分子生活的历史,而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中东欧向苏联的体制转变时期。时隔多年后,我们才能意识到当时的以萨特为首的知识分子犯了多大的错误,朱特正是从这一点入手解读:“我着手写的是一份关于民族弱点的个案研究:在政治和伦理上惊人的前后不一,这种前后不一是法国知识分子对极权主义兴起的典型反应。”
这本书与大多数研究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朱特引入了美国和中东欧知识分子的对比视角,以此观照法国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行为。比如法国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更大,美国知识分子更接近专业技术人员,当他们在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时,经常受到公众的质疑。法国知识分子与中东欧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更为接近,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力更大,像哈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后来的文人总统,像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一呼百应,应者云集。要知道在那个时期,最有名也是最愚蠢的一句口号就是,宁愿跟随萨特犯错,也不跟随阿隆正确。且不说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盲从祸害了一代人,至少证明了法国知识分子对公共巨大而可怕的影响力。
但是法国知识分子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恰恰不是通过介入政治,而是通过文学、哲学和诗歌等艺术美学的手段影响发挥作用的,所以当他们有一天离开熟悉的领域,把介入政治当成一种责任,很容易就成了极权政治利用的可怕力量。换句话说,当公众对萨特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有着非同一般崇拜的时候,这群知识分子也陷入了对苏联和斯大林政权的迷恋,而这种迷恋致使他们丧失掉原来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成为了众多盲从者中的普通一员。
在朱特看来,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他们甚至也不是特立独行。他们在共同体中生活,寻求尊重,害怕他人的否定,他们追求事业,他们期望成功,他们敬畏权力。从“二战”到年,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圈中,在迫害、暴力和死亡如此重大的人类议题上,当我们在人群中几乎听不到什么不同意见的声音时,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也许需要稍微惊讶一点的是,在上述的这些议题上,反而有着不同寻常的融洽。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知识分子的这种复杂特性,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也会愚蠢,也会犯错。知识分子的错误,相比普通人影响更为深远,因为他们不仅仅会犯错,还会利用手中的话语权为自己的错误进行粉饰性的合理性辩解,甚至赋予自己的过错一种悲剧性英雄的色彩,影响更为恶劣。
无论是身为历史学家,还是公共知识分子,朱特都会警惕这种对知识和历史的利用。历史学家的天职是讲述历史,因为操控历史是二十世纪封闭社会的共同特征;而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不丧失独立清醒的立场和判断,让人们了解历史:“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
思郁您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