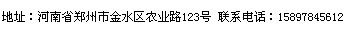男孩天生患有怪病,妈妈抱一下就会骨折,医
我天生就是个“瓷娃娃”,从被子里翻身、打喷嚏、甚至妈妈抱抱我,我都有可能骨折。
医生曾断言过我活不到13岁。
然而到了十三岁,我发现我还活着。
我们是一群成骨不全症患者,从出生起,就患上了这种发病率仅为1/的罕见病,俗称“瓷娃娃”。
我们的骨头比正常人脆很多,还在襁褓里时,妈妈抱着我换了个姿势,我的大腿骨直接断成两截,照X光,骨头的断端像被菜刀利落砍过。
这是最近一次手臂骨折的X光片
这具身体受到任何轻微的磕碰就会骨折,严重时还会出现不可逆残疾,甚至死亡。
我必须安安分分地活着。
三四岁,我眼看着同龄小孩都自己走路了,只偶尔向父母撒个娇,被抱起来走一段,而我还是趴在父母肩上,被抱去吃饭、上厕所、睡觉。
七八岁时,父母仍是我的支撑,唯一变化的是,偶尔他们外出,我就坐在他们提前摆好的一张小板凳上,脚尖轻轻蹭着地,听窗外小孩的嬉闹声。
我很确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如果我还活着,一切仍会是这样。
那个时候爸妈应该比现在老了不少,他们的腰背一点点垮下去,而我仍像一个巨型玩偶,挂在他们身上。
这种“正常”正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变得不正常。
1
小时候看电视,我记得最深的一幕是皇帝穿龙袍。
三个宫女围着,两人把龙袍摆正、展开,剩的一个捧着头冠在一边等。等皇帝穿好,再蹲上蹲下地整理。整个过程,皇帝只需要伸伸手臂。
因为我的病,爸妈也习惯了把我当“皇帝”供着。
我的穿衣流程是固定的:妈妈拿过我的上衣,一手拎着领子,一手拉住袖口,替我把衣服撑开;爸爸扶起我的胳膊,一点点往衣袖里套。
他们全程看起来都很紧张。
我们都记得,一次我的胳膊被袖子绊了下,只听一声清脆的“咔擦”,爸爸慌乱地停下动作时,我的胳膊已经断成两截,一片红肿。
我很想做点什么,但看着父母担心的眼神,又觉得少动、或者不动,就是帮他们最大的忙了。
皇帝穿戴整齐后,要坐轿子去上早朝,我也差不多,父母的怀抱就是为我定做的“轿子”,我每天就乘着这顶“轿子”,晃荡在几十平米的屋子里。
去客厅吃饭,但没法喝凉水,那会刺激脾胃让我打嗝——我的身体受不了这样轻微的震动。
每一次打嗝带动的脊柱会让我疼得直抽气。
凉水灌入喉咙我也可能打喷嚏,这时我只好捏住鼻子,张开嘴,大口呼吸。
去卫生间洗澡,爸爸将我放在一张小凳子上,拿起淋浴器,缓慢地揉搓我的身体。
有时我会听见叹气声从身后传来,在溢满水雾的狭窄房间里,怎么也散不掉。
就连我上厕所也得大人看着。因为骨骼发育不全,体型过于瘦小,我坐在马桶上随时可能掉进去。
一天结束,和皇帝回寝宫一样,我也被父母送回卧室睡觉,那是我极少数可以为自己做主的时候——决定睡姿。
我盖着被子想翻个身,得先打弯膝盖,让一只脚掌在床上踩实了,撑起棉被内部的空间,以防转动时被子的重量直接扭断我的大腿骨。
准备姿势摆好后,我会抓紧床单,从脚心开始,屁股、腰椎、背脊骨、肩胛以床为支点,一边慢慢翻动,一边竖起耳朵,仔细听是否有声音从骨头缝里蹦出来。
这些就是我从小被要求做到的“正常”。
2
电视里皇帝不会跑去宫里做饭的地方,我也一样,8岁前从没进过自家厨房。
每次被父母抱到饭桌前,我只需要张开嘴,就能填饱肚子。
我忍不住想,我平日里吃的这些饭菜是怎么来的?一次趁爸妈不在家,我决定偷偷去厨房看看。
当时我还没有轮椅,父母去上班就会把我放在一张小凳子上。
我的双腿骨折最多,慢慢弯成了两座拱桥,悬在半空,脚尖刚刚能碰地,全身上下,只有手臂能被轻度使用。
没做手术的右手,骨折错位以后,打了石膏固定,自然愈合了
那天,凳子变成了我的腿,我双手抓住凳子边缘,脚尖轻轻蹭地,尝试让身体小幅度前后扭动。原地打转了一会儿,凳脚开始在地板上摩擦,发出第一声尖锐的“刺啦——”
我却觉得悦耳。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向前“走”。
这几步路走得艰难,我很快没劲了,但浑身虚脱的感觉却像在说:我活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刻。
推开厨房门的瞬间,我看到了架着锅炉的台子、案板和刀、顶上有一个会“抽风”的机器,还有各种瓶瓶罐罐。
眼前的场景和电影、我梦里的完全不一样,我的父母不是魔术师,厨房里也没有魔法,所有东西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真实存在着。
伸长脖子,身体前倾,我试着伸手去够那些玻璃罐子——
指尖就快碰到时,我没来由地感到害怕,触电般缩回手。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身体已经给出本能的反应,脑袋里响起:“得千万小心,别碰那些尖锐、易碎的东西。”
从小到大,类似的话我听过很多遍,这是父母好心的嘱咐、提醒,此刻,我却觉得这更像一种警告,是我绝不能触碰的底线。
两手重新扶住凳子,我挪着离开厨房,一点点撤回自己的世界。
那次厨房历险以我的狼狈退场结束,我当时很为自己的畏惧感到沮丧。
但这些畏惧的源头,其实是围绕着我们的那些声音。
我尝试跟几个患成骨不全症小妹妹的父母沟通,“得了这个病不意味着没法动,有些部位适当活动,反而利于骨头生长。”
但每次都被立马拒绝。
“我家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万一磕了碰了,骨折了怎么办?我就希望她能早点懂事,可以保护好自己。”
我懂这种恐惧,这也曾是我爸妈每天都在念叨的。
几次意外骨折后,爸爸觉得我坐凳子也很危险,只有躺平,把弯曲的小腿放在枕头上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受伤。
我连唯一的小板凳也保不住了。
这回我没有妥协,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烦闷一下子涌上来,人生第一次,我对爸爸发了火——
“我需要自由,需要活动,而且双腿一直静养,肌肉只会越来越萎缩,直到彻底废掉!”
八年了,我没有一天用这两条腿走过路,甚至连站都没站过,坐着时,至少我能感受到它们是存在的。
而躺在那儿,我只能不断被提醒:你的腿已经废了,没了,不可能用得上了。
一番激烈争吵过后,爸爸最终同意我坐凳子,但得等他下班到家后,才可以。
我能活动的范围本就不大,客厅、卧室、洗手间。
被限制使用板凳后,我一天有近十二个小时只能坐在沙发上,对着天花板,我的世界就和我看到的一样,一片空白。
这一次,我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后撤了。
3
“这个孩子活不过13岁。”
帮我确诊的老教授说,13岁是人体二次发育的关键节点,骨骼会迎来新一轮生长——
但对于成骨不全症患者来说,那可能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
随着身体发育,骨骼不断抻长,骨质却没有提升,成骨不全症患者的身体就好像一根木条,越长越容易被掰断。
我的身体每骨折一次,我的父母就越相信老教授的判断。
所以曾经爸妈对我最大的期望仅是:安分地活到13岁。
我被这种期望按着头,活了12年零9个月,只有自己知道,它快要压不住我了。
一次躺在沙发上,我突然起急,对着空气蹬腿。几乎是同时,我的右腿发出断裂的声音。
父母见状,赶忙找来纸壳子,快速剪成四个长方形,用绳子固定在我的大腿四周。
等我缓过来些,爸爸从背后抱起我,妈妈托住我屁股,医院。
我疼得五官扭作一团,眼泪糊满整张脸。
直接疼死过去?还是又一次憋不住时,害自己崩断整根骨头?
距离13岁还剩3个月时,我给自己写了一封遗书。
一直以来,父母都希望我能老实地活着,我也基本做到了,这么多年,他们照顾我很辛苦,也算没白费。
“如果...有...下辈子...”,可谁知道人到底有没有下辈子,皇帝都不行。
“像...正常人...”,是可以自己穿衣、吃饭、上厕所,和别的小孩一起玩,不用被人抱来抱去的正常人。
我的手颤得厉害,额头不停冒汗,整件衣服都被汗打湿。
白纸上,一行字写得像蚂蚁在爬。我怎么也写不下去了。
回想这十二年,我疼过、害怕过、愤怒过,但停下笔的那一刻,我被极深的无奈与不甘包裹了。
没有比“等死”更坏的结果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为什么不再争取下?
当晚,我向父母提出要去逛超市。禁不住我反复叨叨,爸爸勉强答应了。
我从衣柜里翻出一条长牛仔裤,遮住打弯的两条腿,被爸爸抱着出了门。
一路上,不断有人向我们投来奇怪的目光,有的大爷大妈忍不住问:“这孩子这么大了,怎么还要你抱着?”爸爸就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等几小时后回到家,脱下牛仔裤,我的两条腿已经捂出了大片痱子。
但这些不愉快在自由面前,都被我甩得干净。
“自由”原来是有味道的,食品柜台油滋滋的肉香,洗护柜台好闻的花香,我大口呼吸着各种商品混杂的空气,越发想要变成一个正常人。
我决定迈出第一步——医院,给我的腿做手术。
如果能站起来,我靠自己就可以去很多地方。
4
在网上搜索了上百条相关新闻后,我发现有一家可以医院。
说服爸妈带我去治疗是最艰难的一环,让他们抛掉十几年的恐惧和想法并不简单。
“医院离我们家太远了,多半是白跑一趟,路上还可能出意外,你还是老实待在家里。”医院的小广告,第一反应就是我在找事、瞎折腾。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好用笨兮兮,也是我唯一能用的办法——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他们身后磨叨。
那段时间,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就是挪凳子。
我双手扶住凳子两边,同一侧的手和腰一起向前发力,左右交替。因为不熟练,起初我“走”得很慢,我还在客厅,爸妈已经进了卧室。
他们只当我是心血来潮,过几天就好了。
但我没有放弃,白天大人不在家,我就挪着凳子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反复练习。
几天下来,我已经能很熟练地用凳子“走路”了。
等到第四晚,我终于抢在爸妈要进卧室前,用凳子在门口把人“拦”了下来。